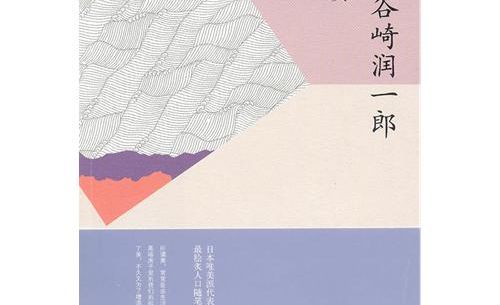
by朱岳
小说家,著有《蒙着眼睛的旅行者》、《睡觉大师》等
2012年3月,我换了工作,去一家图书公司做文字编辑,工作就是伏案看小说。我读了两遍《都柏林人》,三遍《大亨小传》(也译作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),三遍《天使,望故乡》,三遍《长夜漫漫路迢迢》,两遍《希腊神话故事》,三遍《秘密武器》,四遍《雪落香杉树》,此外还有一些,不一一列举了。像《都柏林人》、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这样的书,我很久以前就买过,但一直没读完。这回就像过去的惰性受到了惩罚,连续读了几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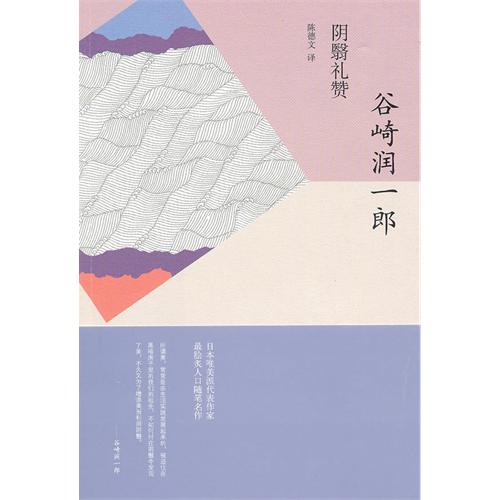
(日)谷崎润一郎/著
陈德文/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每天上班看稿看个头晕眼花,余暇的时间再想读点东西是件挺难的事。我记得最开始恢复属于自己的阅读,是早晨利用上班前吃早饭的时间,在麦当劳重读了一遍川端康成的《独影自命》,在我断断续续读川端康成的时候,麦当劳在反复播放曾轶可的两首歌,一首叫“Forever 21”,一首叫“Baby Sister”。《独影自命》是川端康成五十岁时写的一系列回忆录的结集,结果在我脑子里,它与曾轶可的歌声融合在了一起,还颇为合拍,此后我一听到曾轶可这两首歌就想到川端康成,一读川端康成,就不自觉地哼哼起曾轶可的嗲歌。
到了夏季,麦当劳的冷气不足,这样的阅读也难以为继。这是个难熬的夏天,印象里只读了几本小册子。其中谷崎润一郎的《阴翳礼赞》,很适合在厕所阅读。我读的这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,陈德文译,开本很小,接近口袋本,拿着十分方便。而且书的内容也屡屡涉及如厕,并有许多生动的品评,其中一篇文章题目就叫“厕所种种”。有些段落写得舒缓、优美,譬如:“我每次到京都、奈良的寺院,看到那些扫除洁净的古老而微暗的厕所,便深切感到日本建筑的难能可贵。客厅固然美好,但日本厕所更能使人精神安然。这种地方必定远离堂屋,建筑在绿叶飘香、苔藓流芳的林荫深处。沿着廊子走去,蹲伏于薄暗的光线里,承受着微茫的障子门窗的反射,沉浸在冥想之中。或者一心望着外面庭院里的景色,那心情真是无可言表呢。”
后来我又找来谷崎润一郎随笔文集的一个老译本,叫《饶舌录》,却只读了前面一百多页就放下了。
夏天之所以难熬,于我不仅是因为暑热,还因为内心的焦灼。我好像迎来了所谓的“中年危机”。严重的时候,我会感到“绝望”像热浪一样,在我心里翻涌。我从十八九岁就开始读各种哲学书,有些问题思索了不下十年之久,但并没面对过这种绝望感。有两本小书给了我很大帮助,它们都属于“牛津通识读本”,是双语对照的,一本叫《佛陀小传》,作者是卡里瑟斯;一本叫《尼采》,作者Michael Tanner。两本书开本小,又都很薄,大概每本也就三五万字,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我想,只有知道了绝望,才有可能理解佛陀或者尼采,他们的听众或读者应该是中年人。
还有一本也许更为特殊的书,《太阳与铁》,是三岛由纪夫的作品,我读的也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,读得一头雾水,但又挺着迷。它讲的大概是语言与肉体的关系,而重心被放在肉体一方。三岛讲的是他用肉体从太阳与铁那里直接学来的东西。我只能说,这是一本激励人锻炼身体的小书。读完之后,我积极地锻炼了三个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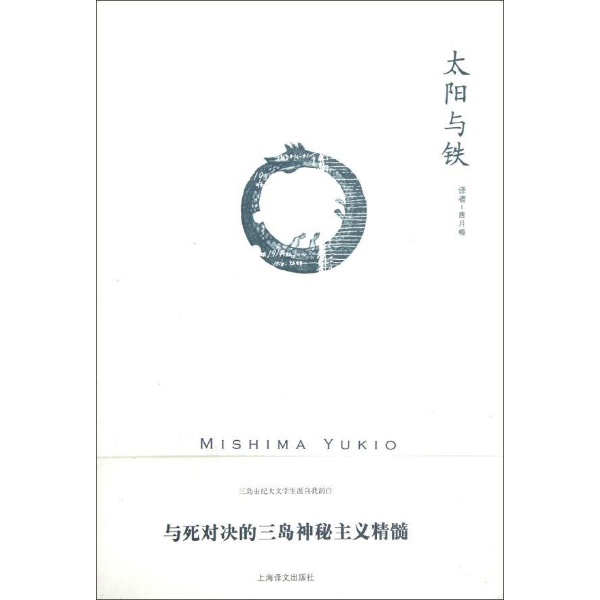 (日) 三岛由纪夫/著
(日) 三岛由纪夫/著
唐月梅/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
这就是助我度过酷夏的几本书。天气转凉以后,我读了三岛由纪夫的《晓寺》,这是一年来唯一一本我利用余暇读完的长篇。我喜欢其中“第一部”,就是讲本多到泰国和印度旅行的部分,涉及印度教和佛教的内容特别精彩。附带一提,这一年我好像老是接触到“印度”主题,除了这本《晓寺》,我还读到一篇格非老师的游记,叫《印度纪行》,他笔下的印度带有轻喜剧的氛围,渺远、广阔,不那么落后,也不那么神秘、酷烈。再有就是读了奈保尔的《幽暗国度》,是为了工作,读后只记下奈保尔的一句话:“情欲就像怜悯,是希望的改良品。”到了接近年底的时候,又看了李安导演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,也涉及印度教,很喜欢这部电影,不过并没去读原著小说。
秋冬交替之际,重读了一遍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。这些年,我每到这一时节就重读一次《雪国》。一读开头: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……”就进入恍兮惚兮、旧梦重温的状态。直到前不久我才意识到,这部小说讲的并非一个爱情故事,它表现的不是那种坚定、平静的感情,而是飘忽的、梦幻般渗透进风景的悲悯,对美的哀吊。
这一年阅读的一个感悟就是,生活环境有所变化的时候,重读自己熟悉的作品是一种慰藉,也有机会获得新的理解。
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