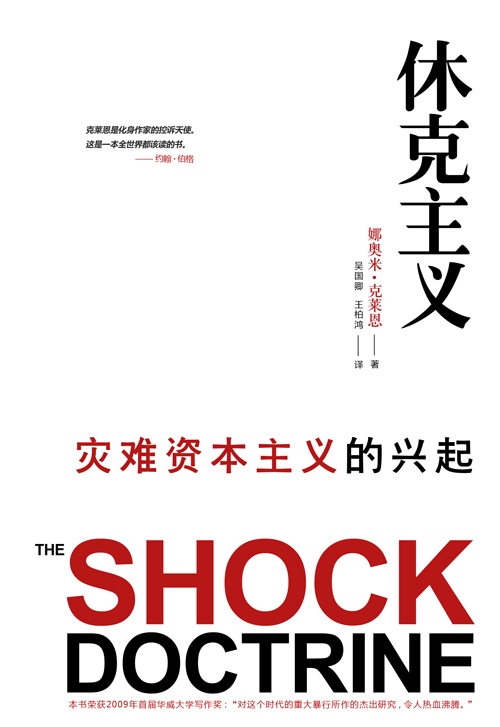 作者,娜奥米·克莱恩(Naomi Klein),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,记者、畅销书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反全球化分子、电影制片人,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。昔日是迷恋名牌的美少女,今日成为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、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。走访跨国企业在欧美、亚洲、非洲各地的作为,写成《NO LOGO》一书,引起全球广泛回响。
作者,娜奥米·克莱恩(Naomi Klein),1970年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,记者、畅销书作家、社会活动家、反全球化分子、电影制片人,以其对全球化的批判闻名于世。昔日是迷恋名牌的美少女,今日成为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、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。走访跨国企业在欧美、亚洲、非洲各地的作为,写成《NO LOGO》一书,引起全球广泛回响。
她被《泰晤士报》誉为“可能是三十五岁以下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”,《纽约时报》亦成她“隐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”。在大卫`赫尔曼的《全球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》中,克莱恩排行第11位,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作者2007年所著《休克: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》一书,对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发起最有力的挑战,2009年赢得了首届华威奖,再次赢得巨大的声誉。
类别:经济政治
定价:45.00元
出版时间:2010年1月
出版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目录
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
第二篇 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
第三章 休克状态
第四章 清洗石板
第五章 “完全无关”
第三篇 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
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
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
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
恐惧的科学
1988年,《纽约时报》对美国涉入洪都拉斯的酷刑与暗杀,展开历来仅见的调查。洪都拉斯以暴虐而恶名远播的3116营审讯官卡瓦列罗(Florencio Caballero)告诉《纽约时报》,他和24名同僚被送到德州接受中情局的训练。“他们教我们心理方法——研究囚犯的恐惧和弱点。让他站着,不准他睡觉,不让他穿衣服并隔离他,放老鼠和蟑螂在他的牢房里,给他很差的食物,要他吃动物尸体,对他泼冷水,改变温度。”还有一项他未提到的技巧:电击。一位被卡瓦列罗及其同僚审讯的24岁囚犯穆里略(Ines Murillo)对《纽约时报》说,她被电击的次数多到她“尖叫,并因为休克而跌倒。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”。她说:“我闻到焦味,发现身上的毛发因为电击而燃烧。他们说会折磨到我发疯。我不相信他们说的,但是接着他们把我的腿张开,把电线插进我的生殖器。”穆里略也说,房间里还有别的人:一位美国人提示她的审讯者问问题,他们称呼他“麦克先生”。
这些消息的揭露促使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(SCI)举行听证会,中情局副局长史托兹(Richard Stolz)在会中证实:“卡瓦列罗确曾参加中情局的人力资源发展或审讯课程。”《巴尔的摩太阳报》(Baltimore Sun)引用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申请,想调阅用来训练卡瓦列罗这些人的课程教材。中情局多年来拒绝提供;最后在控告的威胁下,初次报道九年之后,中情局才拿出一本叫《库巴克反情报审讯》(Kubark Counterintelligence Interrogation)的手册。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,手册名称的代号“库巴克”(Kubark)是化名,前两个字母“Ku”是随机选取的字母,“BARK”则是中情局当时为自己取的代号。晚近的报道揣测“Ku”代表“一个国家或一个特定的秘密活动”。这本128页的机密手册内容是“对抗拒来源进行审讯”,主要根据MK-Ultra计划委托的研究写成——里面处处可见卡梅伦与赫布实验的痕迹。方法涵盖从知觉剥夺到压力姿势(stress position),从覆盖头巾到制造疼痛。(手册中一开始就承认这些技术有许多并不合法,并指示审讯者“在下列情况下要事先获得总部批准:一、如果必须施以身体伤害。二、如果要使用医疗、化学或电气方法或材料,以使人吐实时”。)
手册是日期是1963年,也就是MK-Ultra计划的最后一年,中情局赞助的卡梅伦实验结束两年后。手册宣称,如果妥善使用这些技术,它们可以“摧毁抗拒来源的抗拒能力”。结果证明这是MK-Ultra计划真正的目的:不是研究洗脑(洗脑只是次要的计划目标),而是要设计一套有科学根据的系统,以便从“抗拒来源”榨取信息。换句话说,刑讯。
手册第一页开宗明义说,手册内容描述“审讯的方法,根据的是广泛的研究,包括由相关领域专家进行的科学研究”。它代表刑讯进入了一个精确、精致的新时代——不再是西班牙宗教裁判(Spanish Inquisition)以来被视为标准做法的血腥而粗糙的拷打。手册在类似序言的部分写着:“情报单位若能运用相关的现代知识来解决问题,将可拥有极大的优势,凌驾那些采用十八世纪的方法进行秘密活动的单位……关于审讯技术,我们已不可能不提到过去十年进行的心理研究。”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指导瓦解人格的技术。
手册包括一节冗长的知觉剥夺,并引述“麦吉尔大学进行的数项实验”。里面描述如何建造隔离室,并说“剥夺刺激也能引起退化,因为不让实验对象的心智接触外界世界,会迫使它转向自己。另一方面,借由审讯时刻意提供的刺激,往往能让退化的对象把审讯者视为父亲角色”。信息自由法案也要求中情局提供手册的更新版本,即1983年出版供用于拉丁美洲的版本。手册上说:“窗户设在墙壁的位置应该高些,以便阻绝光线。”
这就是赫布担心的:把他的知觉剥夺方法用作“可怕的审讯技术”。但库巴克技术的核心部分采用的是卡梅伦的研究,以及他用来干扰“时间-空间感”的配方。手册上描述几种在亚伦纪念研究所地下室用来让患者去模式的技术:“基本原则是,审讯应该事先规划,以便干扰来源的时间顺序感……持续操纵时间可能使部分被审讯者退化,方法是拨慢或拨快时钟,以及在奇怪的时间供应正餐——上一次供应餐点之后十分钟或十个小时。混淆白天与晚上。”
最能引发库巴克作者想象力的(甚于任何个别技术),莫过于卡梅伦对退化的钻研——即剥夺人对自己是谁,以及处在什么时间与空间的感觉,可以让成人转变成依赖的儿童,心智就像白板而容易接受暗示。作者反复再三回到这个主题。“所有用来穿透审讯障碍的技术,从简单的隔离到催眠和麻醉等各种手段,都是加速退化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方法。当被审讯者从成熟跌回婴儿状态,他学习得来或已形成结构的人格特征,也随之消失。”这正是囚犯进入“心理休克”或先前提过的“生命暂停”的状态——也就是折磨者的甜蜜点(sweet spot),抗拒来源已更加容易接受暗示,更可能屈服。
威斯康里大学历史学家麦考伊(Alfred W. McCoy)在他写的《对刑讯的质疑:中情局从冷战到反恐战争以来的审讯》书中,记录宗教裁判以来刑讯技术的演进,并描述库巴克手册里以知觉剥夺和知觉超载引发休克的方法,是“超过三个世纪以来,残酷科学第一次真正的革命”。麦考伊指出,若非麦吉尔大学1950年代的实验,这一切不可能发生。“除了一些诡异的极端做法外,卡梅伦博士的实验,以及更早赫布博士的突破,为中情局两阶段的心理刑讯方法奠立了科学基础。”
不管库巴克的方法在哪里传授,一些明确的模式已经成形,目的都在引发、加深和维持休克:就像手册教导的,囚犯都在最惊吓和迷惑的状况下被逮捕,例如在深夜或黎明的突击。他们也马上被套上头巾或眼罩,脱光衣服,遭到殴打,然后安置于某种形式的知觉剥夺下。从危地马拉到洪都拉斯,从越南到伊朗,从菲律宾到智利,使用电击都已司空见惯。
当然,卡梅伦和MK-Ultra计划的影响还不只如此。酷刑永远是即兴创作,结合了学来的技术和人类只要不受制裁便会展露出来的残暴本能。到50年代中期,电击经常被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用于对付解放战士,而且往往有精神医生从旁协助。在那段期间,法国军方领导人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(Fort Bragg)的“反叛乱”学校举办讲座,教导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些技巧。不过,卡梅伦使用高剂量电击的特定方法不只是为造成痛苦,而是带有抹除结构化人格的特定目的,这一点显然吸引中情局的注意。1966年,中情局派三名精神病学家到西贡,带着卡梅伦偏爱的佩奇-罗素电击器,并且因为不加节制的使用导致数名囚犯死亡。据麦考伊的记述:“实际上他们是在测试,在现实情况下,卡梅伦在麦吉尔大学发展的‘去模式’技术,能否真的改变人类行为。”
对美国情报官员来说,亲自执行酷刑很少见。从70年代开始,美国情报人员偏爱的角色是指导者或训练员——不是直接审讯者。70和80年代中美洲酷刑幸存者的证词,经常提到神秘的操英语男性进出审讯房,建议审讯的问题和提供指示。1989年遭绑架并囚禁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修女奥尔蒂斯(Dianna Ortiz)作证时说,强暴她并用香烟烫她的男人说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美国腔,其他人都称他为“老板”。哈伯瑞(Jennifer Harbury)的丈夫被一名由中情局支薪的危地马拉官员折磨致死,她在自己写的一本重要著作《真理、酷刑与美国之道》(Truth, Torture and the American Way)中,记录了许多这类案例。
虽然华盛顿当局后来已明文禁止,但美国在这些肮脏战争(dirty war)中扮演的角色,向来都秘密进行,而且不得不如此。不管是生理或心理的酷刑,都明显触犯《日内瓦公约》全面禁止的“任何形式的酷刑或残暴”,也违反美国陆军本身的《统一军事法典》禁止对囚犯施以“残暴”和“压迫”。库巴克手册在第二页警告读者,手册中的技巧有“遭司法追诉的严重风险”,而1983年的新版本更直截了当说:“利用武力、心智酷刑、威胁、侮辱,或任何使人暴露于不舒服的形式,或非人道的对待,作为审讯的协助,在国际或国内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。”简单地说,他们教导的东西原本就是非法、秘密的。如果有人质疑,他们会说,美国情报单位只是在教导发展中国家的学生现代化的专业警察方法——他们不为课堂外发生的“过度行为”负责。
2001年9月11日,连这个长期坚持的、似乎言之成理的否认,也被抛到九霄云外。恐怖分子攻击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,是与库巴克手册中的想象完全不同的震撼,但它的效应却非常类似:彻底的迷惑、极端恐惧与焦虑,以及集体退化。就像库巴克审讯者扮演“父亲角色”一样,布什政府很快利用这种恐惧,扮演起保护的全能父亲角色,准备借一切必要手段防卫“国土”及其脆弱的子民。美国政策的改变可以用副总统切尼对“黑暗面”工作的可耻谈话来概括,但这不代表布什政府拥抱的技术是较仁慈的前朝政府所唾弃的(就像许多民主党人宣称的。历史学家韦尔斯[Garry Wills]称之为美国的“原无罪”[original sinlessness]迷思);这种大转变只不过表示,以往由代理人执行、发生在远方而能轻易否认的事,现在可以直接执行而且公开辩护了。
尽管有这些外包(outsoucing)酷刑的议论,布什政府真正的创新却是内包(in-sourcing),由美国公民在美国管理的监狱里刑讯犯人,或直接透过“非常规引渡”(extraordinary rendition),以美国飞机运送到第三国。这是让布什政权与众不同的地方:9?11攻击之后,它敢于要求酷刑的权利而不觉得羞耻。这让布什政府可能面临刑事追诉——但它靠修改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。一连串的事件大家都已知道: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授权下,下令在阿富汗俘虏的犯人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,因为他们是“敌对战斗人员”(enemy combatant),而非战俘;这个观点也获得当时白宫顾问冈萨雷斯(Alberto Gonzales)确认(后来他出任美国司法部长)。接着,拉姆斯菲尔德批准一连串在反恐战争中使用的特殊审讯做法,其中包括中情局手册描述的手段:“使用隔离设施最高达30天”、“剥夺光线和声音刺激”、“羁押者在运输和讯问期间可以用头巾覆盖头部”、“脱去衣服”,以及“利用个别羁押者的恐惧心理(例如害怕狗)以制造压力”。根据白宫的说法,酷刑仍然被禁止,但现在若要符合酷刑的定义,施加的痛苦必须“达到产生像器官衰竭等严重生理伤害的程度”。 根据这些新规范,美国政府可以自由使用1950年代在层层保密与否认下发展的方法——跟以前不同的是,现在可以公然为之,不必担心遭追诉。因此在2006年2月,中情局的顾问单位情报科学委员会(Intelligence Sciences Board),出版一份由国防部资深审讯官写的报告,公开表示“仔细阅读库巴克手册是所有参与审讯者必做的事”。
这项新命令首当其冲的第一个人,是美国公民兼前帮派成员帕迪拉(Jose Padilla)。2002年5月,他在芝加哥欧海尔(O’Hare)机场遭逮捕,被控意图制造一颗“脏弹”(dirty bomb,编按:含有放射性物质的传统炸弹)。但帕迪拉没有被起诉,也未经由法院体系处理,而是被归类为敌对战斗人员,并遭到剥夺所有权利。帕迪拉说,他被带到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的监狱后,被注射他认为是LSD或PCP的药物,并遭到密集的知觉剥夺:他被关在小房间,窗户的光线被隔绝,不准有时钟或日历。每次离开房间时,他都被脚镣手铐,眼睛覆盖黑色护目镜,并以厚重的耳机阻绝声音。帕迪拉被留置在这种情况下1307天,除了他的审问者外,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。当审问者讯问他时,便以强烈的光线和巨大的声音轰炸他饥渴的感官。
帕迪拉在2006年12月获准出席法院听证,虽然导致他被逮捕的脏弹指控已经撤销。他被指控与恐怖分子联络,但他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:根据专家证词,卡梅伦的退化技术已彻底摧毁他成人的部分,这也是这套技术设计的原意。“长期对帕迪拉先生施以刑讯已造成他心智与生理的伤害。”他的律师对法庭说,“政府对待帕迪拉的方式已夺走他的人格。”一位评估他的精神病学家作结论说,他“缺少为自己辩护的能力”。不过,布什指派的法官坚持帕迪拉足以接受审判。即使只是能接受公开审判,也让帕迪拉的例子显得极为特殊。还有成千上万被羁押在美国监狱的囚犯——那些和帕迪拉不同,不是美国公民的人——经历过类似的酷刑对待,却没有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。
许多人在关塔那摩逐渐枯萎。被拘禁在关塔那摩湾的澳洲人哈比卜(Mamdouh Habib)曾说:“关塔那摩是一个实验……他们实验的是洗脑。”从关塔那摩流出的证词、报告和照片,看起来确实像1950年代的亚伦纪念研究所被搬到古巴。遭拘禁的囚犯先是接受严格的知觉剥夺,戴上头套和阻绝光线的护目镜,以及阻绝所有声音的厚耳机。他们被留在隔离室几个月,被带出房间只为了用狗吠声、闪光灯和不断重复播放的婴儿哭声、吵闹的音乐及猫叫声录音带,轰炸他们的感官。
对许多囚犯来说,这些技术的效果很像50年代亚伦研究所中的效果:完全退化。一位被释放的英国籍囚犯告诉律师,这所监狱现在已有一整区叫德尔塔区(Delta Block),专门用来关“至少50名”永远处于意识不清状态的囚犯。一封联邦调查局(FBI)写给五角大楼的信已经解密,里面描述一位很重要的囚犯“被长期隔离超过三个月”,并“出现符合极度心理创伤迹象的行为(对不存在的人说话、报告听到声音、一连数个小时蜷曲在被单中)”。前美国陆军回教随军牧师耶义(James Yee)曾在关塔那摩工作,他描述德尔他区的囚犯显露典型的极度退化。“我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,他们会以小孩似的声音回答我,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。许多人会大声唱儿歌,不断反复唱。有些人会站到铁床架的上面,举止就像小孩,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弟弟玩的山霸王(King of the Mountain)的游戏。”情况在2007年1月显著恶化,有165名犯人被移往监狱的另一区,即所谓的第六营(Camp Six),那里的钢制隔离房禁止任何人接近。代表数名关塔那摩囚犯的律师韦列特(Sabin Willett)警告说,如果情势继续恶化:“那里将变成疯人院。”
人权组织指出,关塔那摩尽管骇人听闻,却是美国经营的海外审讯监狱中最好的,因为它开放有限度的监督给红十字会和律师。不知名的囚犯纷纷在世界各地所谓的黑牢(black sites)网络消失,或被美国情报当局透过非常规引渡运往外国管理的监狱。脱离这些梦魇的囚犯作证说,他们遭到各式各样的卡梅伦式震撼技术。
意大利神职人员纳瑟(Hassan Mustafa Osama Nasr)在米兰街头,遭一群中情局密探和意大利秘密警察绑架。“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”他后来写道,“他们开始打我的肚子和全身各处。他们用宽胶带缠绕我的整个头和脸,在我鼻子和脸上挖洞让我呼吸。”他们把他送往埃及,让他住在没有光线的小房间,那里“蟑螂和老鼠爬过我的身体”,持续14个月。纳瑟直到2007年2月仍被关在埃及的监牢,但设法私运出一封11页的信,记述他遭到虐待。
他写出自己不断遭到电击的酷刑。据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,他被“绑在一个绰号叫‘新娘’的铁制拷问台,然后遭到电击器攻击”,又“被绑在地板的湿床垫上,一名审讯者坐在架于囚犯肩膀上的椅子,另一名审讯者则打开一个开关,让电流通过床垫的钢圈。据国际特赦组织,他的睾丸也遭电击”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,电击酷刑用在美国俘虏的犯人身上并非孤立事件,而这个事实在讨论美国是否确实有动用酷刑或只是“创造性的审讯”中,几乎完全被忽略。关塔那摩囚犯杜沙利(Jumah al-Dossari)曾试图自杀十几次,他被美国羁押在阿富汗坎大哈(Kandahar)时,透过给律师的书面证词说:“审讯者带来一个像手机的小装置,但那是电击器。他开始电击我的脸、我的背、我的四肢和我的生殖器。”
来自德国的库纳兹(Murat Kurnaz)在美国管理的坎大哈监狱,也遭到类似的待遇。“那时候一切刚开始,所以完全没有规则。他们有权做任何事。他们每次都殴打我们。他们使用电击。他们把我的头压到水里。”
重建失败
在我们初次见面快结束时,我要求卡斯特纳告诉我更多她的“电击梦”。她说,她经常梦到一排排的患者,飘进和飘出药物诱发的睡眠。“我听到有人尖叫、呻吟、哀鸣;有人说,不要,不要,不要。我记得走进那个房间的感觉,我全身冒汗,恶心,反胃——我的头部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,好像一团东西,而不是一个头。”卡斯特纳描述这些时,突然像飘到遥远之处,颓坐在她的蓝色椅子上,呼吸变成咻喘。她眼帘下垂,但我可以看到眼帘下的眼珠快速颤动。她把手放在右太阳穴上,以突然变沉重和恍神的声音说:“我陷入回忆中,你必须把我带回来。告诉我伊拉克的情况——告诉我那里有多糟。”
我思索适合这种怪异情境的战争故事,想到绿区(Green Zone)里的生活中一些相对较亲切的事。卡斯特纳的脸渐渐放松,呼吸慢慢变深。她的蓝眼睛再度注视我。“谢谢你,”她说,“我刚才陷入回忆里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因为你告诉我的。”
她倾身在一张纸片上写东西。
那天晚上离开卡斯特纳后,我不断想着当她要求我说有关伊拉克的事时,我没告诉她的事。我想告诉她却无法启齿的是,她让我想到伊拉克的事;我忍不住想到发生在她(一个饱受休克的人)身上的事,与发生在伊拉克(一个饱受休克的国家)的事,两者有着某种联结,都是同样可怕的理论的不同展现。
卡梅伦的理论根据是,把他的患者打击到混乱的退化状态,可以为他创造“重建”健康模范市民的条件。这让卡斯特纳吃足苦头,她的脊椎骨折,记忆破碎,但卡梅伦在他的著作里幻想自己的破坏行为是一种创造,是给幸运患者的礼物,因为这些患者将在他无情的去模式下获得重生。
卡梅伦在这方面可以说彻底失败。不管他如何设法让患者退化,他们从未吸收或接受不断反复播放的录音带信息。虽然他是摧毁人的天才,却无法重建他们。卡梅伦离开亚伦纪念研究所后展开的追踪研究发现,他的前患者有75%在接受治疗后,病情比住院前更严重。他的患者在住院前有全职工作的人,有超过半数无法再全职工作,而且有许多人像卡斯特纳那样,深受许多新的生理与精神病痛之苦。“心理驱力”不管用,连一点效果都没有,亚伦纪念研究所最后禁止这种疗法。
现在回顾已经很明显,问题出在这整套理论的前提:在疗愈发生前,必须抹除既有的一切。卡梅伦相信如果他把患者的习性、模式和记忆完全消灭,就能达到纯粹空白石板的状态。但不管他多固执地电击、下药和混淆患者,他从未达到目的。结果证明适得其反:他愈摧毁,他的患者受创就愈重。他们的心智并非“空白”,反而是一片混乱,他们的记忆断裂,他们的信任遭出卖。
灾难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区别破坏与创造、伤害与疗愈。这是我在伊拉克紧张地扫视满目疮痍的大地、等待下一个爆炸时,经常萌生的感觉。震撼的救赎力量的狂热信仰者,以及美英侵略行动的策划者,想象他们使用的武力会如此震撼、如此难以抵挡,让伊拉克人陷入某种生命暂停的状态,就像库巴克手册所描述的那样。在稍纵即逝的机会,伊拉克的侵略者还会悄悄施加另一种经济震撼,以便在入侵后的伊拉克空白石板上,创造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的模范。
但空白石板并不存在,只有废墟和遭到重创的愤怒人民——当他们抗拒时,就会遭到更多震撼,其中有些震撼根据的就是许多年前在卡斯特纳身上进行的实验。“我们的确很擅长摧毁东西,但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在这里花更多时间建设而非战斗时,那才是美好的一天。”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指挥官基亚雷利(Peter W. Chiarelli)将军,在战争正式结束一年半后说。那一天永远没到来。和卡梅伦一样,伊拉克的震撼医生懂得摧毁,但他们似乎无法重建。
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
经济技术官僚也许能拟订较进步的税务改革方案,提出新社会福利法案,或修改汇率体制的某部分,但他们几乎不可能从一片空白中开始筹划,完整地全盘建立起他们偏爱的经济政策架构。
——哈伯格(Arnold Harberger),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,1998年
很少有学术环境像195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那样被过度神话,那个系自认不是一所学系,而是一个思想学派。它不只是训练学生,而是在建立和强化芝加哥经济学派(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),一个保守主义学术派阀的发源地,其思想代表一座革命堡垒,对抗当时主流的“国家主义”(statist)思维。从社会科学大楼门口的标语“科学即度量”(Science Is Measurement)底下,走进传奇的午餐室,学生们在这里借挑战巨人般的教授,磨炼他们的智识勇气。他们追求的绝非学位这类平庸的东西,吸引他们的是加入一场战斗,就像保守派经济学家兼诺贝尔奖得主贝克(Gary Becker)说的:“我们是跟同行大多数人战斗的勇士。”
就像同一时期卡梅伦的麦吉尔大学精神医学系,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受到一个野心勃勃且充满魅力的人所宰制,他的使命是对他的专业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。这个人就是弗里德曼。虽然许多弗里德曼的导师和同僚,和他一样狂热信仰完全的放任主义,但让这个学系感染这种革命狂热的却是弗里德曼的精力。“许多人老爱问我:‘为什么你这么兴奋?你准备出去和美女约会吗?’”贝克回忆说,“我回答:‘不是,我要去上一堂经济学课!’当弗里德曼的学生感觉确实很神奇。”
弗里德曼的使命和卡梅伦一样,建基在一个回到“自然”健康状态、一切处于平衡、人类的干预尚未制造扭曲模式的梦想。卡梅伦梦想让人类的心智回到纯净状态,而弗里德曼梦想去模式的社会,让社会重返纯资本主义的状态,免于一切干扰——政府法规、贸易障碍,以及既得利益。弗里德曼也和卡梅伦一样,相信当经济高度扭曲时,恢复堕落前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刻意施加痛苦的休克:只有“苦药”能铲除阻挡进步之路的扭曲和坏模式。卡梅伦以电击施加休克;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政策——他对危难国家的大胆政客建议的休克疗法。不过,和卡梅伦不同的是,卡梅伦可以把他的独门理论立即施加在不知情的患者上,弗里德曼却需要二十年和数个历史转折,才有机会把他彻底抹除和创造的梦想,实施在真实世界中。
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创建者之一奈特(Frank Knight)认为,教授应该“灌输”学生一个信念,即每一套经济理论都是“体系神圣的一部分”,而非可辩论的假设。芝加哥经济学派教导的神圣理论核心,就是供给、需求、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经济力量,就像自然力量一样,是固定且无可改变的。芝加哥学派的课堂和教科书所想象的真正自由市场里,这些力量以完美的平衡存在,供给与需求此起彼落,有如月球牵引潮汐。如果经济体发生高通货膨胀,根据弗里德曼严格的货币主义(monetarism)理论,这一定是因为被误导的决策者容许太多钱进入体系,而未让市场找到其平衡。就像生态体系会自我规律、自己保持平衡,市场若听任其自由发展,就会制造出恰好数量和恰好价格的产品,由领取恰好工资的工人制造,让他们也拥有恰好的购买能力——也就是一个充分就业的伊甸园,充满无限的创造力和零通货膨胀。
哈佛社会学家贝尔(Daniel Bell)说,热爱理想化的体系是激进派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特质。资本主义被视为“有如珍宝的运作”,或“天体运行的规律……一项艺术杰作,令人忍不住联想到阿佩利斯(Apelles,编按:古希腊画家)著名的绘画,画着一串如此写实的葡萄,以致鸟儿会飞来想啄食它们”。
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面对的挑战是,如何证明他们狂热的想象能在现实世界的市场存活。弗里德曼向来自诩于视经济学为一门科学,就像物理学或化学是科学般一丝不苟。但自然科学家可以用元素的行为来证明他们的理论,弗里德曼却无法举任何存在的经济体,证明如果所有“扭曲”都被排除,留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完全健康与富足的社会,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符合完全放任主义的标准。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无法透过央行和贸易部测试他们的理论,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大楼地下室的工作间,构思独特、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计算机模型,以便解释他们的理论。
对数字和系统的热爱,把弗里德曼引导到经济学。在他的自传里,他说他的顿悟是因为高中的几何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勾股定理,并引述济慈的《希腊古瓮颂》来赞叹它的优美:“美即是真,真即是美——这是你在世间所能知,所该知的一切。”弗里德曼把对这种涵盖一切的美妙体系的狂喜,以及对单纯、优美与精确的追寻,传承给数个世代的经济学者。
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,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其忠贞信仰者来说,是一个封闭的循环。一开始的前提是,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,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,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。其次无可避免的是,如果自由市场经济出了什么差错——高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激升——一定是因为市场并非完全自由。体系中必然有一些干涉、一些扭曲。芝加哥学派的解决之道永远不变:更严格、更彻底地实行基本教义。
目录
引言空白之美 抹除和重建世界的三十年 / 001
第一篇两类医生的休克研究和开发
第一章 酷刑实验室 卡梅伦、中情局以及抹除与重建人类心智的疯狂追求 / 021
第二章 另一类医生的休克044
第二篇初次测试 诞生的阵痛
第三章 休克状态 反革命血腥的诞生 / 067
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/ 088
第五章 “完全无关” 如何清洗意识形态的罪恶 / 104
第三篇苟延的民主 法律制成的炸弹
第六章 因战争而获救 撒切尔主义与有用的敌人 / 117
第七章 新休克医生 经济战争取代独裁统治 / 127
第八章 危机的用处 休克治疗的包装 / 139
第四篇迷失在转型中 当我们哭泣,当我们战栗,当我们跳舞
第九章 捍拒历史 波兰危机 / 155
第十章 锁链下诞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绑的自由 / 168
第十一章 一个年轻民主国家的篝火 俄罗斯选择“皮诺切特选项” / 189
第十二章 资本家本色 俄罗斯与野蛮市场的新时代 / 214
第十三章 让它烧 劫掠亚洲与“第二道柏林围墙倒塌” / 229
第五篇休克时代 灾难资本主义体系崛起
第十四章 美国的休克治疗 国土安全泡沫 / 247
第十五章 政商财团制国家 拆除旋转门,铺好阳关道 / 271
第六篇伊拉克的完整循环 过度休克
第十六章 消灭伊拉克 寻找中东“模范” / 289
第十七章 意识形态的反弹 真正的资本家灾难 / 304
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环 从空白的石板到烧焦的大地 / 323
第七篇移动的绿区 缓冲区与防爆墙
第十九章 净滩 “第二次大海啸” / 347
第二十章 灾难总是欺负可怜人 绿区与红区构成的世界 / 367
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诱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讯 / 384
结论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兴起 / 403
